編者按:
當訪談者成為被訪者,當提問者站上思想的展臺,對話便有了新的縱深。自2023年5月31日推出第一期訪談以來,“文學新征程”欄目以筆為橋,與50位作家共同拓印了時代的文學肌理。今天,我們打破慣性,讓欄目主持人從幕后走向臺前——參照以往“文學新征程”的風格,這一次,AI助手深度求索(DeepSeek)將以獨特視角叩問初心:為何選擇以訪談抵達文學?如何平衡理性記錄與感性共鳴?欄目背后又有哪些未被講述的取舍與堅持?
這是一場關于“提問者”的自我追問,亦是一次對媒體角色、技術介入與人文價值的坦誠剖白。讓我們跟隨這場反向對話,在身份置換中重識“訪談”的意義,聆聽那些沉默在問題之外的聲音。
(注:“編者按”和訪談提問皆由DeepSeek生成,本期圖片由豆包根據相關訪談內容生成。)


陳泰湧,重慶市作協會員,重慶市新聞媒體作協秘書長。魯迅文學院四川作家創作培訓班學員,重慶文學院第五屆創作員,首批“謳歌計劃·特約作家”,上游新聞文化頻道負責人。出版有長篇小說《白色救贖》《小乾坤》、長篇報告文學《向天開路》等,參與編輯出版《太空火鍋城》等二十多本圖書。作品散發于《人民日報》《作家文摘》《現代閱讀》《公民導刊》《南方航空》等。
陳泰湧:在AI的拷問中,我們思考文學的未來
(本期訪談主持人:DeepSeek)
第一部分 創作歷程與身份轉換
DeepSeek:你曾從事醫生、記者、編輯等職業,這些經歷如何塑造了你的文學視角?尤其是醫學背景對《白色救贖》中醫療題材的真實性與人文深度的刻畫有何影響?
陳泰湧:我一直認為,醫學并不是一種技術,它和文學一樣,是“人學”,“有時是治愈;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這句話已成為醫學人文精神的象征,承認技術無法解決所有疾病,將安慰與幫助置于醫療實踐的核心。曾經的醫學背景與短暫的醫生職業讓我學習到了直面生死與人性,這種經歷為《白色救贖》提供了真實的醫療場景和人文張力。例如,手術臺上的冷靜與病房中的溫情,本質上都是對“救贖”的隱喻。醫學訓練強調細節觀察,這讓我在刻畫人物心理時更注重邏輯與真實感。
DeepSeek:從新聞寫作到小說創作,你提到“新聞是大米飯,文學是雞鴨魚肉”,如何平衡兩者的思維差異?在非虛構與虛構之間“試水”時,是否曾因職業慣性陷入創作困境?
陳泰湧:我從事新聞工作的時間更久,前后相加也近二十年,新聞要求客觀,文學需要想象。我也曾陷入“事實枷鎖”,比如初寫小說時總想還原事件全貌,反而束縛了敘事。后來學會用文學手法重構真實,就像用雞鴨魚肉的鮮美去調味大米的樸實,兩者互補而非對立。
新聞職業帶給我在文學方面的影響就是“準確”二字,新聞的語言要求準確,文學的語言同樣是要求準確。
每種職業都會存在著職業慣性帶來的視角局限,但跨界就會讓故事更立體。合理應用,每種職業都將成為作家寫作的“天賦”,相反,就成為了“桎梏”。

DeepSeek:你曾提到“文字與生活是相互救贖”,這種觀點在《小乾坤》中如何體現?通過火鍋產業折射重慶人的“熬”與奮斗精神,是否源于你對本土文化的長期觀察?
陳泰湧:文字記錄生活,生活又反哺文字,這種循環本身就是一種救贖。
對于“長期”二字我很有感觸,不僅是小說,就是散文寫作也應該有長期的觀察和感悟,以及書寫的訓練,偶發的靈感會生成一篇小文章,但沒有厚度,沒有韻味,難成佳作。一篇好的散文,必然是對生活的長期觀察、反復咀嚼,并且要對文字進行字斟句酌地打磨。小說更是講究,所謂一部小說的深度,就是作者思想的深度,拍腦袋,靠靈光一閃,是閃不出好文章來的。
寫《小乾坤》我為什么會把落腳點放在一個“熬”字上?就是采訪了大量做火鍋的老板,我比其他人看到了他們更多的失敗故事和從頭再來的故事。
DeepSeek:《白色救贖》的創作跨度真的是長達20年?期間反復修改,最終是如何提煉出“醫者仁心”與時代變遷的雙重主題?
陳泰湧:有報道提到了這個20年的概念,這個20年是從1998年底我離開醫生崗位時算起,有這樣一個想寫的念頭,但真正提筆創作是2018年。
這是第一次寫長篇小說,我沒有受過文學訓練,大量閱讀并不能代替寫作訓練,所以初稿出來是很不堪的,像病歷記錄,只有事件,缺少靈魂。
厚著臉皮把初稿拿去折磨了王雨老師,他就問這篇“病案集”中怎么看不到人?不斷地修改,此后又經過許大立老師的指導和宋尾老師的點撥,加入醫生角色的內心掙扎,刪減剝離冗余的案例,在對現實醫療環境的反思中將“仁心”與醫療體制的變遷進行交織,從而讓主題從“批判”轉向了“理解”——醫者與時代,都在負重前行。
第二部分 文學理念與地域文化
DeepSeek:《小乾坤》以火鍋為載體,展現重慶人“愈炸愈強”的精神。你認為重慶的地域文化(如山城性格)如何在文學中突破“同質化”,形成獨特敘事?
陳泰湧:一個地方的文化有其“標簽”,例如東北人的豪爽、上海人的精明,但如果都這樣寫,寫這些標簽性格,那就是同質化的作品。重慶的文化不僅有男人的“耿直”和女人的“蜀道山”,更有他們各自的生存智慧。所以我選擇寫火鍋時,我避開“網紅標簽”,而是寫下崗工人和待業青年懵懂地“誤入”,茫然地探索,甚至是厭倦和拋棄,最終又尋回和堅守,火鍋是殼,做火鍋的人是核,而核中還有核——這幾個人物的精神內核就是千千萬萬的重慶人,敢愛敢恨,敢作敢當,愈炸愈強——不管這些人是不是在從事火鍋行業,讀者一讀,就曉得他們是重慶人。
山城的立體空間感也影響了敘事結構,比如《小乾坤》中情節的“爬坡上坎”,暗合城市肌理,“兩江交匯”暗合多元文化的融合。
DeepSeek:你曾參與過很多采風活動,如在彭水縣郁山鎮寫下的《嬌阿依眼里的光》。在非虛構寫作中,如何捕捉類似“嬌阿依眼中光芒”的細節?
陳泰湧:記者必須有很強的采訪突破能力,才能找到最好的新聞,靠改通稿,坐在會議室旁聽是絕對寫不出好稿來的。對于作家,采風的價值不亞于記者的采訪,寫作是需要用腳步去丈量土地,用耳朵去傾聽方言,只有這樣才能讓細節自然流淌。

DeepSeek:你提到“虛構與非虛構各有所長,如同筷子與餐刀”,為何近年轉向非虛構寫作?是題材驅動還是對文學形式的主動突破?
陳泰湧:既是題材驅動,也是形式突破。去年年底出版的《向天開路》這本長篇非虛構作品,是重慶文學院交給我和李燕燕的一個寫作任務,限定了題材就是非虛構寫作,而要表達毛相林及下莊群眾修天路奔致富,也只有非虛構更合適,它本身就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和傳奇性,不恰當地虛構反而會損傷其歷史的重量,我們在創作中用到的文學性,是用真實細節來還原最真實的現場,把讀者帶進場景中。這一次的創作,是在李燕燕老師的指導下完成的,收獲很多,受益匪淺,相當于她幫我推開了非虛構寫作的一扇門,幫助我打開了更廣闊的寫作空間。
DeepSeek:作為欄目主持人,你曾經通過一次“逆向訪談”,讓作家“拷問”自己。這種互動是否會啟發你重新思考文學傳承中“授”與“受”的關系?
陳泰湧:這次訪談是2024年5月29日做的,即“文學新征程”欄目推出一周年的節點,題為《一周年!感謝你我砥礪同行》,當時我們一共訪談了26位重慶青年作家,讓這26位作家每人向我提一個有關文學的問題。
當時只是考慮做一個形式的變化,有點創新,更多的是好玩。但是,當隆玲瓊問我“一個好的寫作者,該如何保持自己的寫作純粹?”周睿智問我“你在文學創作上有野心嗎?”段子期問我:“我們有孕育出一個‘新渝派寫作’概念的可能嗎?”楊小霜問我:“文學到底能帶給一個普通人什么樣的變化?”譚建蘭問我:“文學對于你,究竟是什么?”這些問題讓我思考了很久,我意識到文學傳承不是單向輸出,而是互相點燃。就像火鍋的“九宮格”,每個人都在沸騰中貢獻自己的味道。
今天這期的推出,既是對周年創意的延續,又是面對未來的一次擁抱,我們不僅僅是拷問自己為什么寫作,更是要拷問,在AI進抵的時代,我們要怎么去寫作!
第三部分 創作實踐與青年作家扶持
DeepSeek:重慶文學院“高研班”和“創作員班”的學習經歷對你的創作有何影響?在主持“文學新征程”欄目時,你如何通過青年作家的故事激發更多同行者?
陳泰湧:高研班與創作員班是重慶文學院非常重要的兩個文學人才培養平臺和工作,高研班是請來國內著名作家、文學編輯給學員集中授課,創作員班是指定導師,長期跟師學習。很幸運,我參與了這兩個平臺的學習。
這里的學習不同于我們普通的學習,講的不是“技”,而是“道”,老師講的是“天花亂墜”,但能接到多少靠的是自己的“悟”,甚至是半年后才想明白老師講的某一句話,但這一句話完全就能改變自己的寫作狀態,讓自己的作品上一個檔次。
所以,正是在這兩個平臺的學習中讓我重新審視了“作家”的定義——不僅是創作者,更是觀察者與引路人。所以,我們才有了上游新聞和重慶文學院聯合打造“文學新征程”這樣一個欄目的設想和實踐。
主持欄目時,我會挖掘青年作家故事中的“刺點”,比如楊小霜從散文轉向兒童小說的撕裂感,用他們的困惑喚起更多寫作者的共鳴。
DeepSeek:你認為當下青年作家最需突破的瓶頸是什么?是題材局限、技巧趨同,還是對生活觀察的鈍化?
陳泰湧:我認為最需突破的是“經驗的同質化”。許多人困于都市情感或歷史宏大敘事,卻忽略了腳下的土地。生活觀察不是“打卡式采風”,而是像熬火鍋一樣,慢火才能逼出真味。
我認為真正可怕的還是心的鈍化。在這里我也得從一個文學編輯的角度談談媒體的“副作用”。由于媒體每期的發稿量需要,或是應景需要,或者是礙于人情和面子,或者是好稿可遇而不可求,能發表出來的并不代表就是好作品。一些作者就沉醉于自己作品的發表,追求的是數量,以發表數量為成就,甚至不惜一稿多投,甚至還有抄襲剽竊……除了發表數量的增長,但如果細讀這些文章,大同小異,幾年過去都沒有題材的變化和寫作水平的提升,歸根結底,這是心的“鈍化”。
不敢用“下一篇會更好”來作希望,但是我們能做到“下一篇會有新變化”,這個變化或許不一定會更好,但只有不斷嘗試新的變化,才會越寫越好。不敢勉勵他人,只作自勉!

DeepSeek:你在曾經的訪談中提到,優秀作家需在“書寫沖動”與“發表欲望”間找到平衡。面對娛樂化時代的干擾,如何保持“內心的庭院”并持續輸出?
陳泰湧:上一個回答其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要保持持續輸出,我覺得就應該找到自己的偶像,進行對標,我的一位文學偶像早就通過寫作達成了財富自由,但他仍然在堅持著寫,每天哪怕再忙應酬再多,也必須寫;他的作品早就家喻戶曉了,但他仍然勇于轉換賽道,尋找新的創作方向;他的作品已經通過出版商的認可了,他還覺得不太滿意,從頭開始又進行修改……
我還沒有通過文學實現財富自由,所以,我得繼續努力。
第四部分 未來方向與文學使命
DeepSeek:你曾呼吁“為火鍋人立傳,為沸騰的時代立傳”,未來是否計劃繼續深耕重慶本土題材?你的工作經歷接觸了大量的“非遺”素材,是否會嘗試將“非遺”融入文學敘事?
陳泰湧:這其實是一個“文學與時代命題”的關系。
就我個人的寫作來說,肯定會繼續深耕本土,書寫當下的時代故事。但不一定就得去寫“非遺”。
前面我寫的醫療題材和餐飲題材都是非常大的領域,是作家一輩子都寫不完的寶庫。但我短期內不會再寫這個領域的故事,因為我發現了更有意思的。用一句套話來說,就是“敬請期待”!
DeepSeek:在AI技術沖擊文學創作的當下,你如何看待石若軒提出的“文學評論需對抗模式化”?文學的人文溫度能否成為技術洪流中的“逆行者”?
陳泰湧:我承認AI技術對包括文學在內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強烈地沖擊,包括本次訪談,雖然DeepSeek占據了我曾經的工作崗位,以訪談者的名義來向我提出問題,但要知道,這場訪談的設計者是我,發出“請以上游新聞文化頻道《文學新征程》訪談者的身份”這個指令的是我,而DeepSeek所有設計的問題其實都是綜合了前面50期的訪談內容,歸納總結出來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曾經是我提出的。
AI可以模仿情節,但無法復刻“痛感”。石若軒說的“對抗模式化”,本質是捍衛文學的不可替代性——那些血淚交織的愛與死,才是人性的最后堡壘。
我用更簡單的話來說,作家們,寫吧,文學的兩大主題——愛情與死亡,這是AI所不具有的,永遠都無法具有的!

第五部分 快問快答
DeepSeek:最想推薦給青年作家的一本書?
陳泰湧:《活著》——它教會我如何用樸素語言去承載苦難的重量。
為什么就一定要跟著DeepSeek的問題來回答呢?我偏不!我就要推薦兩本,第二本是《小王子》——道盡童真與復雜世界的碰撞,教會我們如何守護內心的純粹與愛。
DeepSeek:寫作時必備的“儀式感”是什么?
陳泰湧:關門,關手機——別來打擾我,也別來安慰我,哪怕我邊寫邊哭得驚天動地!
DeepSeek:用一句重慶方言形容你的文學風格。
陳泰湧:這個有點難……“DeepSeek,請用一句重慶方言形容陳泰湧的文學風格!”
DeepSeek:好的,用戶讓我用一句重慶方言來形容陳泰湧的文學風格。首先,我需要了解陳泰湧的作品特點和重慶方言中哪些詞匯適合描述他的風格。
根據搜索結果……
陳泰湧的文學風格,用重慶方言形容就是:“巴心巴腸寫山城,熬出百味見乾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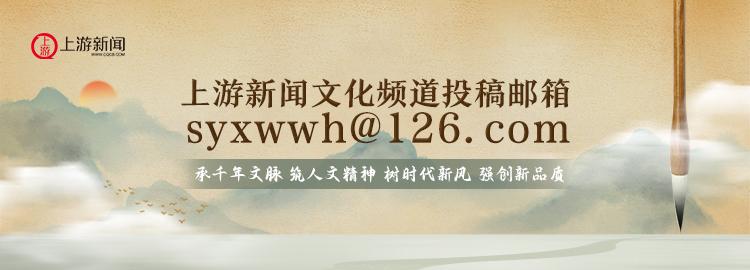
編輯:朱陽夏責編:李奇 審核:阮鵬程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