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節假期剛過去沒多久,關于理想汽車CEO李想的一則年薪披露卻讓不少打工人破防了。
據理想汽車2024年年報披露,理想汽車董事長李想的薪酬其年薪為6.39億元,其薪資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266.5萬元的年薪,另一部分是因公司在2024年達到交付50萬臺的目標而觸發的期權激勵,產生超6.36億元的激勵費用。
年報還披露,除了董事長李想之外,理想汽車的其他高管收入也足以傲視群雄:執行董事兼總裁馬東輝的年收入高達4027.4萬元,CFO李鐵的年收入高達3916.0萬元。
薪酬披露后,有網友在評論區留言:“月薪5000,要10650年才能賺到他的年薪。”的確,在當下經濟環境面臨不確定性之時,新能源車賽道屬于為數不多走在上升期的行業,而行業之間的割裂造成了公眾的不理解。其中的關鍵問題在于,算上期權在內,李想一年6個億的總薪酬是否合理?
財務角度看,無可厚非
理想汽車的薪酬爭議,本質上是美股會計準則(FASB)下的期權費用確認規則與公眾認知的沖突。
根據財報,李想2024年的6.39億元收入中,6.36億元為“股份支付薪酬費用”,但這筆錢并未產生實際支付,而是會計上對期權潛在價值的預估。
理想汽車近日也在對公眾的回應中指出,李想如果想拿到這筆激勵費用,除了需要完成公司設定的銷量目標外,還需要額外支付一筆不菲的費用。以5月6日美股收盤價格25.68美元計算,李想若要執行該期權方案,不僅沒有任何收益,還需要倒貼3200萬美元,相當于人民幣2.3億元。
首科綠匯ESG負責人高艷輝認為,理想汽車從創立以來實現了“從無到有”,在將市值從零做到千億的過程中,創始人拿到億級的薪酬激勵,是否就是不合理?“如何評價一家企業創始人、董事長的價值,以及薪酬是否合理,在公司治理層面和大眾認知角度存在差異是可以理解的,”高艷輝說道。
需要強調的一個背景是,理想汽車在2020年IPO時依賴單一產品和技術路線,發展前景曾被部分媒體及分析師“看衰”,特別是增程式電動車在當時還存在較大爭議:一是電池安全性問題,當時消費者普遍擔憂電池在高溫環境出現的自燃問題;二是電池耐用性問題,例如在冬天低溫環境下存在“拋錨”現象。
鑒于這些問題,當時消費者對新能源汽車的信心是不足的,哪怕有國家補貼支持,但一眾造車新勢力的發展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基于這一點考量,李想在當時簽下高風險的激勵協議本身就承擔了較高的風險。
一個直接的數據是,在2020年一季度,理想汽車仍在虧損。當時的李想曾在多個公開場合談到成本控制策略:“理想汽車超過3200人的團隊,只有兩個VP,連高級總監都寥寥無幾。行政要求出差經濟艙都必須買折扣最低的,經濟酒店都要兩個同性在一起住。”
商道咨詢合伙人郎華指出,李想被披露的薪酬存在其合理性:“從財務角度看,公司在設置股權激勵的時候往往考慮的是公司的長期發展,以及對于創始人和公司發展之間的關系。尤其對于新能源車這種高速發展的行業而言,股權激勵的形式能將公司高管與公司長期的發展做綁定,讓公司發展得更好。”
其中合理性的關鍵在于,股權激勵是否與公司業績增長趨勢同步,如果業績無增長且市值不斷縮水,但薪酬卻一直在增長還附帶大量期權激勵,那就是不合理的。
“不過,權威評級機構曾對創始人薪水給出過一個合理性參考,首席執行官在一個報告期的總獎勵薪酬是否超過其他指定高管的中位數薪酬的三倍以上,這算是一個客觀的參考,”郎華說道。
治理角度看,并非都說得通
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李想的薪酬之所以引發如此大的輿論爭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披露透明度”不足,繼而引發了公眾的質疑。
例如有網友就吐槽道:“年初定個80萬輛目標,發現完不成,降到60萬輛;半年過去,發現還完不成,再降到50萬輛。年底一盤算,總算完成了,然后獎勵自己6.4億。”話糙理不糙,客觀反映出薪酬設置不透明帶來的治理隱患。
郎華認為:“對于公眾而言,冷冰冰的一串數字不太容易被理解,公司在年報中是否能作出更細節的解釋說明?來自公眾的質疑其實對品牌的長期發展不利。”
的確,李想這一激勵協議在此前鮮少被提及,其具體提出及施行的時間并不透明,官方回應也無法完全打消公眾質疑。
從ESG評級看,理想汽車在MSCI的ESG評級為AAA,這在國內幾乎是碾壓般的表現。但高艷輝認為,這則輿論風波反映出理想汽車在公司治理上仍然有值得改進的地方。除了剛才提到的信息披露透明度以外,理想汽車還未將高管薪酬與ESG指標相掛鉤。
虎嗅ESG組認為,高管薪酬不與ESG目標相掛鉤不僅可能導致高管過度關注短期財務目標,忽視環境、社會等長期議題,削弱對高風險行為的約束,還可能加劇高管與股東、員工等利益相關者的目標沖突。
一個直接的證明是,2024年理想汽車曾陷入較大的裁員風波,發生事件在MEGA發布后不久。表面上看,裁員是對過往擴張迅猛與業務發展之間矛盾的一次糾錯,但究其本質,架構調整和裁員行動反映出理想汽車對接下來業務發展的預判。
在隨后的一個月,媒體又曝出理想汽車突然緊急召回部分關鍵崗位的被裁員工。反復橫跳的操作凸顯出企業內部治理還存在可以優化的空間。
結合李想年薪來看,無疑給人一種“一將功成萬骨枯”之感。高管與員工薪酬的鴻溝擴大,則可能引發S“社會”層面的“相對剝奪感”,這與ESG所倡導的“公平薪酬”原則相沖突。
“國際、國內主流ESG披露規則、評價標準的發展趨勢是,關注高管薪酬與ESG指標掛鉤的情況。企業在ESG管理中除了制定戰略、設定目標、有行動有披露之外,考核是能夠讓ESG管理成為閉環的重要手段,”高艷輝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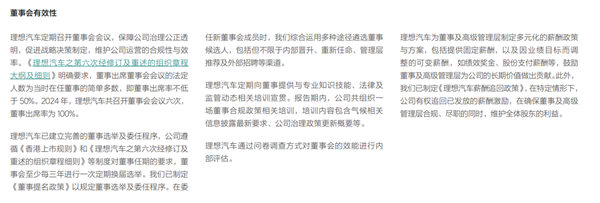
薪酬政策中未提及與ESG指標掛鉤,圖源:理想汽車2024年ESG報告
“一家公司的CEO如果薪酬績效考核能夠和ESG績效掛鉤的話,會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高艷輝指出:“如果CEO和高管團隊的薪酬激勵與ESG表現掛鉤,那么公司在作出管理決策的時候就會有更全面的考量,包括在員工權益和人文關懷方面可能會有更周全的方案。這也是為什么我們需要企業關注ESG的原因之一,它能夠切實改善企業對社會責任的履行。”
將高管薪酬與ESG指標掛鉤聽起來容易,但執行起來卻并不容易。高艷輝認為,目前很多上市公司的實踐現狀是,從ESG治理上看什么都有,既有治理架構又有制度,但實際工作卻在表面上,ESG管理落到實處還需要一個過程。
值得注意的一個指標是,員工流失率從2023年的22.3%上升至2024年的38.2%,近乎翻倍。有媒體統計,理想汽車2024年一共新招員工12959人(社招 校招),但一共流失12302人,猜測與裁員相關。
企業也存在難處
理解企業在ESG治理層面存在障礙的一個視角是,外部經濟性與企業競爭內卷相疊加,為企業推行ESG帶來挑戰。
根據公開數據及行業報告,2022-2024年期間,中國新能源車企倒閉數量超過50家,實際淘汰率超過90%,行業洗牌速度遠超預期。同時,行業價格戰進入白熱化,企業陷入從產品競爭到全產業鏈的廝殺。
而從宏觀看,外部地緣政治事件不斷,經濟形勢也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在這么“卷”的市場下生存是第一位的,出現裁員等現象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是,一個企業只有在能活下去的條件下才能去談如何把ESG做得更好,這是當下企業在做ESG時遇到的共性問題,”高艷輝說道。
外部經濟性如何影響企業ESG目標的構建?郎華舉了一個例子。“例如我們在考察‘S’(社會)層面的時候,供應鏈管理是其中相對重要的一個指標,但圍繞這一點很難制定目標,因為制定了目標后就會提升整條價值鏈的成本,你的供應商也會為了你做很多改造,從而提升產品的成本,在業績上對企業構成壓力,影響企業未來的發展。”
郎華進一步指出,尤其在特朗普關稅預期下,未來企業出現的裁員信息料想會持續發生,企業如何兼顧自己的生存與可持續發展?這是比較矛盾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理想汽車在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表現相比去年又有了進步,在總溫室氣體排放因汽車銷售額大漲的客觀條件下,依然實現了排放密度的減少:2022年總量為104733噸二氧化碳,密度為2.3噸二氧化碳/百萬人民幣營收;2024年總量為322278噸二氧化碳,密度為2.2噸二氧化碳/百萬人民幣營收。
但從現實層面而言,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還不夠深入人心,在“一個品牌是否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有成就”和“售車時的直接折扣”之間,國內消費者更愿意選擇的是后者。
高艷輝認為這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化有關:“歐洲市場消費者對于可持續品牌概念的接受度很高,甚至愿意為此付出一定的溢價,比如在10%的溢價內,消費者會更愿意購買帶有可持續理念的品牌商品,但在國內市場,可持續消費還處于更早期的階段,這與消費理念、消費能力有關。”綜上,國內企業的ESG之路還處于初期,尚且需要耐心。
總結而言,李想薪酬引爆輿論的背后的確有信息披露不夠的因素在,但作為一家新能源電動車企的創始人,其從0到1將理想做到千億規模,拿一定的激勵期權無可厚非;從環境角度看,理想若一年賣出50萬輛,其減少的潛在碳排放(相對燃油車)在未來將對環境帶來持續的益處。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